说到睡前故事;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,由何人起先搞这个事情,最后才形成一种普遍的习俗的。
当然;我们是在讲故事,不是写什么报告,又或者是新闻稿,也就用不着搞什么严谨的调研什么的了。
之所以在这里提起讲睡前故事这件事,那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,它就是由我已故的奶奶通过睡前故事,讲给我和那时尚且年幼懵懂的弟弟听的。
至于我是谁?大家喊我傻根儿就好!,为毛会叫这么个名字了?和本卷故事无关,所以洒家也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了,以后会有一卷故事把我王傻根儿的情况,逐渐向列为看官交代清楚的!(本卷;七瓜婆、讲述清末一位农家女子升仙的故事!)
好了!闲言少叙;接下来咱们就不在多言,我就直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,奶奶给我讲的好些个故事之中;我记忆还算深刻的一个!
要说这个故事就少不了得,先要介绍一下我奶奶,毕竟我奶奶的“世界”与我们可以说是不同的,有些故事也只有在那种不同的“世界”才有存在的可能。
我奶奶是清朝末年生人,她原籍是我们邻村的,因为两家祖上都在县城做生意,规模都还不算小属于有不小的铺面那种。那时的县城也不大,清末的大环境又动荡不安。
外加那时离我们村子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“山寨”,对就是电视里那种打家劫舍的土匪寨子。
当然;现实中的土匪山寨也没有现在电视中演的那么明火执仗、肆无忌惮,动不动就百十号人,在聚义厅里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什么的。
现实情况是;山寨、聚义厅的确实都有,但是一般情况下山寨里是没什么人的,就留守几个接头人在山寨。
留下这些人的作用也很简单;就是专门与周遭的青皮、二流子接头,这些个不务正业的家伙,就是这些土匪天然的眼线。
所以平日里这山寨,也就这么大猫小猫三两只。遇到有官兵搜捕、又或者被打劫的苦主纠集人来报复,这几人就早早跑进深山躲起来,至于其他的土匪的去向,则就是真正的“藏兵于民”了。
山寨的山脚下有个叫连丰的村子,这个村子虽然外表看似乎除了穷了点儿之外,与当时的其他村子并无两样。但是世上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,一来二去、年深日久。逐渐周围村庄和县城的人都是知道了;其实这个村子,就是这伙山贼土匪的真正“匪巢”!
当时这个村子里的七八十户人家,几乎家家都出了人去“山寨”入伙。这整个村子的人,白天看着是苦哈哈、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但是到了“山寨”一有下手目标,头人召集令一下,那拎刀的、提棒的、汇聚起来,立马就能“变”出七八十条凶神恶煞般的持械悍匪!
那时候是晚清末期,天下动荡不休。加之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又处于腹心位置,官兵久疏战阵、缺少训练武备松弛不说;更过分的还是被带兵的老爷们吃空饷,所以这些所谓的官兵,战力到底能有几何?自是不说也罢!
而所谓的官兵剿匪,实际上;不如说是,例行公事的游行来的贴切。官兵出来剿匪的缘由,也从来压根就不是,什么清剿匪患、保境安民什么的。
官兵之所以出来“剿匪”,也只是被上面拿了别人好处的大老爷,逼迫下的无奈之举。所以让他们出来溜达一圈还行,要是真让这些所谓的官兵,去真刀真枪的和这些个悍匪拼命那是想都不要想的!
上面那些个官老爷,实际上也是清楚这些个情况的,可不要认为这些个腐败的,封建阶级旧官僚就都是笨蛋。他们要是笨蛋的话,早就被无处不在的倾轧给搞死了!
虽然他们也明白官军战力堪忧,但是毕竟吃了、拿了别人的。且不说;清剿匪患、保境安民本就是他们的分内之事,就单单吃人嘴短、拿人手软,迫使他们也不得不派出官兵,去“游行”一遭来堵别人的嘴。
而那些个土匪也是“识趣”,一旦官兵来围剿,他们就退避三舍。从来不与官府正面对抗,所以那些个只想着搂钱,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念的封建官僚,也就从未想过要真的想办法铲除治下的这伙土匪。
“郎有情妾有意”这一方退让,一方完全不追究,这官、匪就这么“无声”却很默契的相互呼应着。
由于我们这地界的地理位置;从地图上来看的话;大约是国家版图正中心腹地位置,所以;虽然县城是着实不大,但是南来北往的过路客商却是着实不少的。
而之前所说的这伙白日为民,夜里为盗的土匪,虽然凶悍但因为没有马的缘故,这些家伙却终究只是土匪,可不是什么传说中来去如风的马匪。也可以说就是一伙“坐地虎”,他们不是马匪,这“硬件”问题也牢牢的限制了,这伙悍匪的活动范围。
这也就注定了;这群家伙在劫掠过往客商的同时,也就只能对周围的的一些地主富户下手了!
而上面说了这么多,看似与我们刚才要介绍的,我奶奶的生平貌似没什么关系。至于与我们要说的睡前故事,则貌似更是八竿子打不着?
其实不然;之所以浪费口水,啰嗦上面这些个官官、匪匪的破事。那是因为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婚事,就是被这种大环境下被迫促成的。
之前也说了;我家和我奶奶家,那是在两个村子的。虽然这两个村子相邻,但是在那个普通出门都要靠草鞋步行的年月,这两村人之间虽会有些往来,但却绝对不会很频繁。
平常人家即使嫁到邻村的姑娘,一年到头也难得回趟娘家。所以在正常情况下;我爷爷和奶奶是不大可能结合到一起的。
有人肯定会疑惑;我刚还不是说了,有嫁到邻村的姑娘吗?为什么现在说到了我爷爷、奶奶这里又会说;正常情况下,他们不大可能会走到一起了?
这里我要让大家特别想故意的是;上面几句话中的两个词,一个是“平常人家”、另一个就是;“正常情况”!
先说这第一个“平常人家”,这里的意思却不是说;我爷爷有什么天生的特异之处,与别人又什么外观或者性格上的不同。简单来说;就是当时也就是爷爷小时候,出门是会有个跟班看护。(这个看护;不是所谓书童,又或者是恶仆狗腿子什么的。在当时清末那个动荡的年代里,虽然一般人流动性不大。但是;有些个活不下去乞讨的,又或者那些游方的道士、和尚什么的,以及令人深恶痛绝的拍花子的人口贩子,却都是这些为数不多流动人口中的“主力军”!小孩子独自外出在外玩耍,遇到前几类还则罢了。要是遇到拍花子的,那就基本是有去无回了!小孩子嘛、你要想一直,给他关在家里不让出门,那也明显是不现实的。尤其是男孩子!所以;当时家里给爷爷请的这个看护,更多的是扮演着保镖的角色。当然了;有这待遇也是因为,爷爷是太爷爷长子的缘故,在那个长幼有序的年代里,为了家业能平稳传承。爷爷这个将来注定了要继承家族产业的嫡长子,有些别人没有的特殊待遇,在当时来说是很正常的情况。)
村子逢人都要喊他声少爷。虽然都是乡里乡亲的,大家这么喊我爷爷;也确实有几分打趣的成分在里面。
但是谁也不能否认;以我家当时的家境,我爷爷还真能算是位少爷!虽然我们家那时在村子里也就一百多亩田地,(注;当时我家还是那种家族式的,太爷爷那一辈就有兄弟三人,各种亲属家眷的一大家子加起来就有二三十人。在加上家里长年请的三个帮工,加之那个年代也没有现在的化肥、良种,所以这一百亩出头的田地的产出,也就刚好满足一大家子温饱略有余粮而已!)比起其他的地主那是多有不如。
但是那时候我家的重心,也不在这土地上。真正赖以为生的营生;那还要说是县城里的,那间规模尚可的布店、加杂货店。虽然这铺面在现代人看来,规模也就那么回事儿。
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月,能在虽然不大却属于南北通衢之地,的县城里有那么一间铺子。那就和今天在市区有间百货大楼差不离,毕竟县城了做买卖的虽然不少,但是因为城池的范围太小。
所以城内的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,所以大多数做买卖的,都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摊位,以及茅草小店。而像我家这种有比较大的正式铺面的,整个县城的拢共也就那么二三十家。
我们村子周围十里八乡的,也就我家和邻村的一家在县城里有这份产业。所以当时;尚且年少的爷爷也能算是名副其实的小少爷。
提到那年头人们的婚嫁观念,想必大多数人能想到的都是门当户对吧?其实不然!在门当户对之前却是还排着,一个亲上加亲、肥水不流外人田。(预知后事如何?且请听下回分解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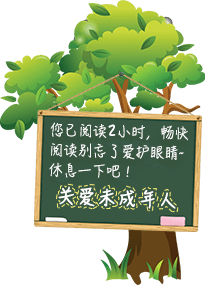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299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299号